勃拉姆·斯托克,吸血鬼伯爵德古拉之父,他在世的时候,是著名演员亨利·欧文的助理,终其一生都在为他的朋友兼老板工作,安排演出,管理财务,琐碎而又忙碌,写小说是他持续一生的业余爱好。
1897年,《德古拉》小说出版之前,其舞台版《不死之人》在兰心大剧院做了一次通读式的表演,亨利·欧文评价“糟糕透了”,拒绝出演德古拉。斯托克为人严肃谨慎,我们无法得知他当时的心情。然而,时隔一百余年,我们或许不知道亨利·欧文,也不知道勃拉姆·斯托克,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德古拉,连温斯顿·丘吉尔和他的父亲都为之痴迷。
然而,德古拉只是勃拉姆·斯托克的众多面相之一,这个形象太著名了,与之相关的影视作品数不胜数,让我们早就忽略了这部优秀的小说。更多时候,提起《德古拉》的作者,我们难免会认为,他不过是一位通俗的惊悚小说作者。
《德古拉的客人》收录了斯托克生前十四篇短篇小说,由他的妻子整理出版。这部短篇小说集展现了斯托克的更多面相,我们会了解到,与其说斯托克偏爱恐怖故事,不如说他通过探索信仰与科学、神秘与实证、预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,来洞察人类心底的原始恐惧。

《德古拉的客人 : 勃拉姆·斯托克奇异故事集》
爱尔兰
勃拉姆·斯托克 著
欧阳耀地 译
漓江出版社
2023年1月
启蒙思想与吸血鬼传说
“当她入梦时,我们以为她已长眠;现在她真的逝去了,我们却认为她只是在沉睡。”
——托马斯·胡德《死之床》
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感叹:“18世纪居然会存在吸血鬼!”
他说的不只是吸血鬼传说,而是18世纪被频繁提起并严肃讨论的重要事件。希腊正教认为尸体入土后会腐烂,只有罗马教派的异教徒才不会腐烂。然而,在罗马教派看来,人死而不朽是永恒之美的象征。就这样,在中世纪,死而复活的现象蔓延开来,成为吸血鬼问题的源头。
在长篇小说《德古拉》中,范海辛教授提到的“亡灵”,原文是undead,指死而不死之人。在这部小说集的同名篇《德古拉的客人》里,“我”在“沃尔帕吉斯之夜”前往山中的村庄冒险,车夫逃跑前告诉“我”,那个村里的人在墓地里发现,死于几百年前的人,面颊红润,嘴巴红色,似乎还有生命。村里的人都逃跑了,他们渴望生活在“死人就是死人,活人就是活人”的地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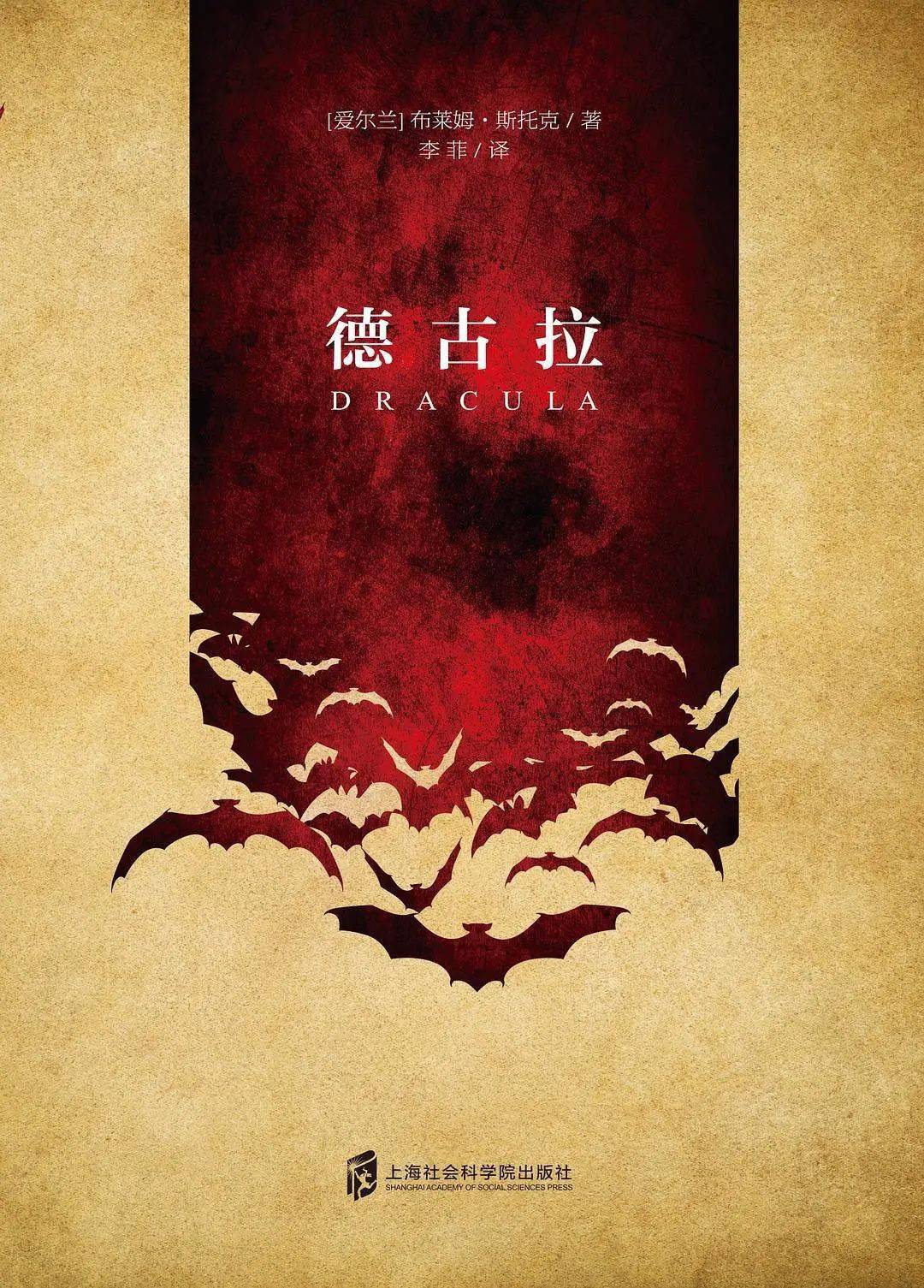
《德古拉》
布莱姆·斯托克 著
李菲 译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2016年12月
据《德古拉事典》介绍,在18世纪,教皇、女王、僧侣、知识分子等精神世界领袖都曾认真、激烈地讨论有关吸血鬼的问题。这实质上是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、科学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决战。直到19世纪,在启蒙思想的光照之下,科学在人类世界观里占据了支配地位,吸血鬼才逐渐丧失魔力,被放逐到小说稗史之中,最终和弗兰肯斯坦、狼人等怪物一起沦为恐怖电影里的丑角。
另一方面,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恐惧。无处不在的屠杀,遍布街头的抢劫,公开示众的断头台、绞刑架,无一不让恐怖气息弥漫整个社会。这时候,人们似乎意识到,杀死吸血鬼的新兴资产阶级,正带领全社会迈向另一个由理性主义统治的世界,这个世界整齐有序却危机四伏。
在《鼠的葬礼》中,追杀“我”的嗜血成性的老兵曾参加法国大革命,《法官的房子》里的绳索曾用来实施绞刑,《印第安妇人》的复仇发生在刑具展示馆中;与之对比,在《命运之链》中,“我”被窗外的影像恐吓,并危害到相亲对象,而当“我”用科学知识解释之后,一切就变得温情脉脉、如沐春风了。
在《法官的房子》里,主人公崇尚高度精确和实事求是的学问,他在古老的房子里备考时遇见了灵异事件:一位曾绞死罪犯的邪恶法官化身硕鼠来搅扰他,故事里医生提出的方案也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。直到最后,我们也很难说清楚,主人公之死,究竟是邪恶法官的亡灵造成的,还是由无意识的臆想导致的。前者有悖于科学精神,后者又很难找到实证根据。如果说鬼魅不存在,那么让我们发狂的究竟是什么?
当恐惧继续弥漫四散,人们发现,实证性的真理无法带来丝毫帮助,反而是沉迷于幻想虚构之中,或许能够得到些许慰藉。所以,启蒙思想的光照越强,人们就越难以抵抗神秘主义的魅惑,就会忍不住去探寻蜷缩在无边黑暗中的未知怪物。

1931年版《德古拉》剧照
肉体噩梦与现实预言
“去证明吧,那个他最憎恶的事实!”
——拜伦《嫉妒》
我们对世界的认识,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立足的现实根基。宗教信仰或科学信仰悬挂在头顶的时候,我们认识的世界、立足的大地均不相同。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提出“我思故我在”来确定实存。身心二元论由此诞生,人们认为,身体是机械,心灵居住其中。
在这部小说集中,多次能看到作者描述精神与肉体分离的感觉。如《德古拉的客人》里,狼趴在“我”身上时,“我”感到温暖,又意识到这是一场“肉体的噩梦”,同时有一种要从某种东西里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。
当我们对理性主义产生质疑,对“我”何以为“我”的信念发生动摇,就会遁入神秘主义里去寻求答案。所以,预言、猜测、想象对现实的介入就成为文学创作的一大灵感源泉。
《老霍根:未解之谜》表面上看是在讽刺金钱崇拜,但其中仍蕴含着对科学实证的反思。“我”被卷入老霍根之死的漩涡里,当地人穷尽一切机会去测量“我”和家人的身体,似乎通过这些数据就能找到“我们”与老霍根死亡的关系。然而,之所以叫“未解之谜”,似乎是指:实证的数据究竟积累到什么程度,才能确证两件事之间的关系?我们通过实证材料,如何才能跨越不可言说的沉默这一道鸿沟?
另一个未解之谜指向人的存在:当老霍根的尸体化成碎片,头颅沉入流沙,世上关于他的痕迹都被抹除,我们是否还能证明他的存在?而“我”在老霍根之死的漩涡中所经历的一切,当所有见证人都已死去,“我”所拥有的经历是否还有意义?如果“我”的经历都不再有意义,那么“我”的存在如何确证?
《预见者》和《吉卜赛人的预言》这两篇有关预言和现实的关系。就前者而论,如果预言不能指定具体事项,那么似乎任何事情都可以纳入其中,这样,判定预言是否有效就毫无意义。然而,预言家告诉“我”,预言并不是为了交易或是消磨时间,我们不能像科学那样,通过揭示某个谜题而让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。科学要求实证,而信仰则要求不能试探你的神。
在《吉卜赛人的预言》中,预言是一个“命题”,背后有一个图像。然而,不同背景的人,会将同一个命题理解为不同的图像,所以,当吉卜赛人说“我”的双手将沾满妻子的鲜血,并不一定是指“我”所理解的谋杀,也可能是妻子摔倒在地上,手被刀子刮破了,而我正握着那把刀。从实证角度来看,预言成真了,但总会让人觉得有点不对劲,因为这与我们内心的恐惧相去甚远,而后者才是我们希望预见到的。
影响的焦虑与影响的复活
勃拉姆·斯托克无缘列进哈罗德·布鲁姆的名单里,在布鲁姆眼里,勃拉姆·斯托克一定与《哈利·波特》、史蒂芬·金同样不入流。然而,在斯托克的小说里,却能看到很多为后世写作者称道的现代写作手法的痕迹。
《印第安妇人》中纽伦堡的“铁处女”酷似卡夫卡《在流放地》的刑具,故事结局也极其相似:刑具的痴迷者爬进刑具并死在其中。《克鲁肯沙滩》中有博尔赫斯经典的“镜像”场景,穿着爱尔兰高地服装的“我”在流沙边缘看见了自己,认为“我”是受生活拖累的人,对面才是更好的自己,当两人刚要碰面,“我”却在流沙下陷之际逃走了,让“更好的我”沉入流沙。
哈罗德·布鲁姆曾提出“影响的焦虑”这一概念,指经典著作给后世作家造成的影响,但在勃拉姆·斯托克的小说里,却是一种逆反的现象:只有读过现代作家的作品,熟悉他们的写作手法,才会在阅读他们前代作家作品时找到趣味。这或许可以称为“影响的复活”。
博尔赫斯推崇爱伦·坡的作品,称赞他从“死亡的另一面”创作惊世骇俗的作品。让博尔赫斯痴迷的不只是故事好看,而是他对神秘的偏好,在爱伦·坡的作品里能够获得慰藉。我们对奇异故事的喜爱,大概就是因为渴望获得慰藉。当日常生活中的困扰无法通过科学实证来排解,我们就只能冒险进入世界的另一个维度,寻找更多的可能性。因此,启蒙时代产生了吸血鬼、狼人、弗兰肯斯坦,今天则催生了生化怪物、反叛的机器人、入侵的外星人。
荣格说,在我们今天的集体无意识中,仍存在着史前世界的野兽和恶魔的栖息地。这是梦的源头,也是艺术的源头。在科学信仰的光照之下,我们难免会耽于精确的实证,摈弃自古以来就有的恐惧和焦虑,导致身体沦为机械,心灵变得枯竭。反倒是以吸血鬼为代表的奇异故事,会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观念产生质疑,让我们复归本源,深刻洞察内心的幽暗角落。
这样看来,我们都该找机会去拜访一下那座孤独高耸于苍凉绝壁的德古拉城堡。
